

作者:刘余莉 聂菲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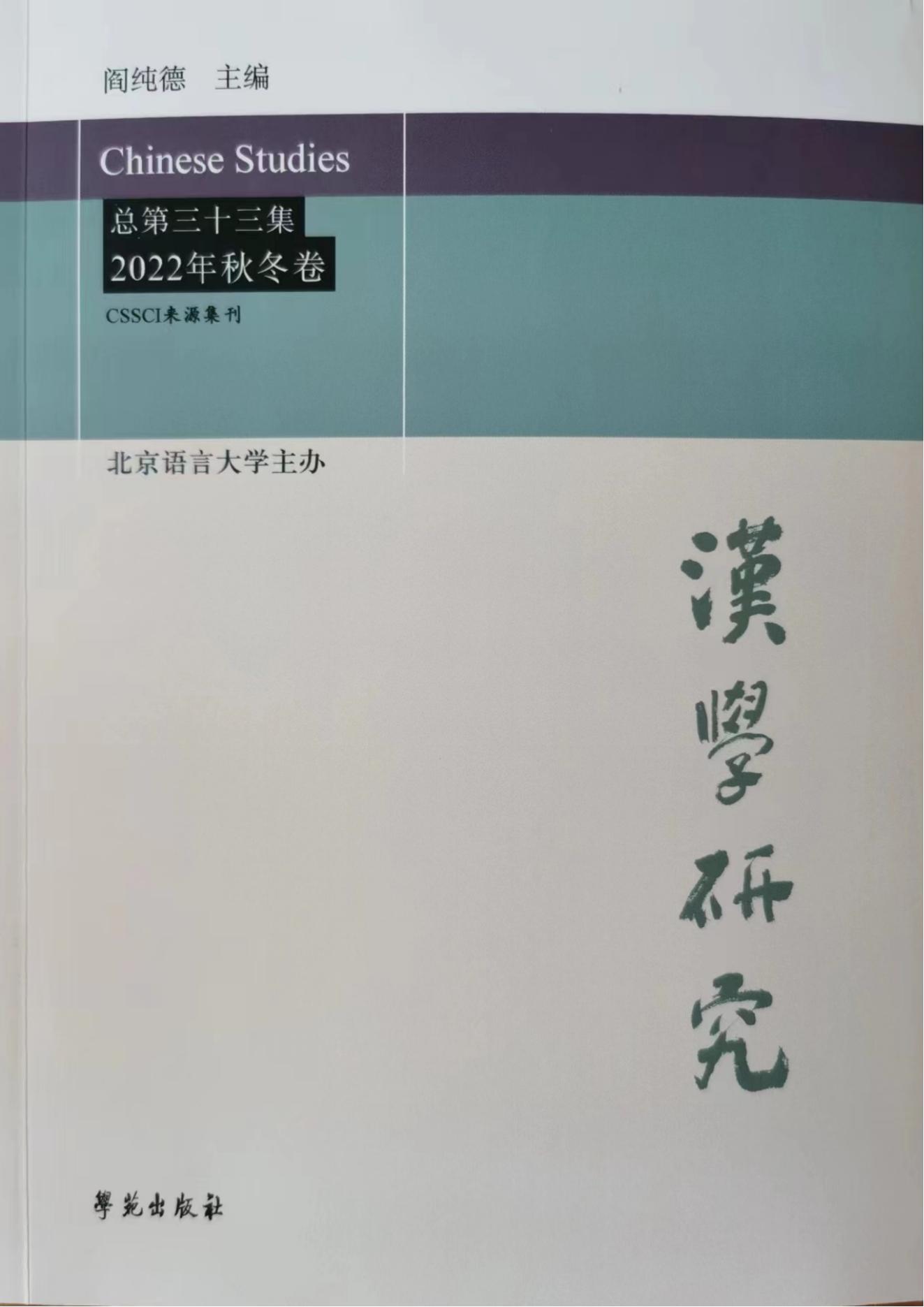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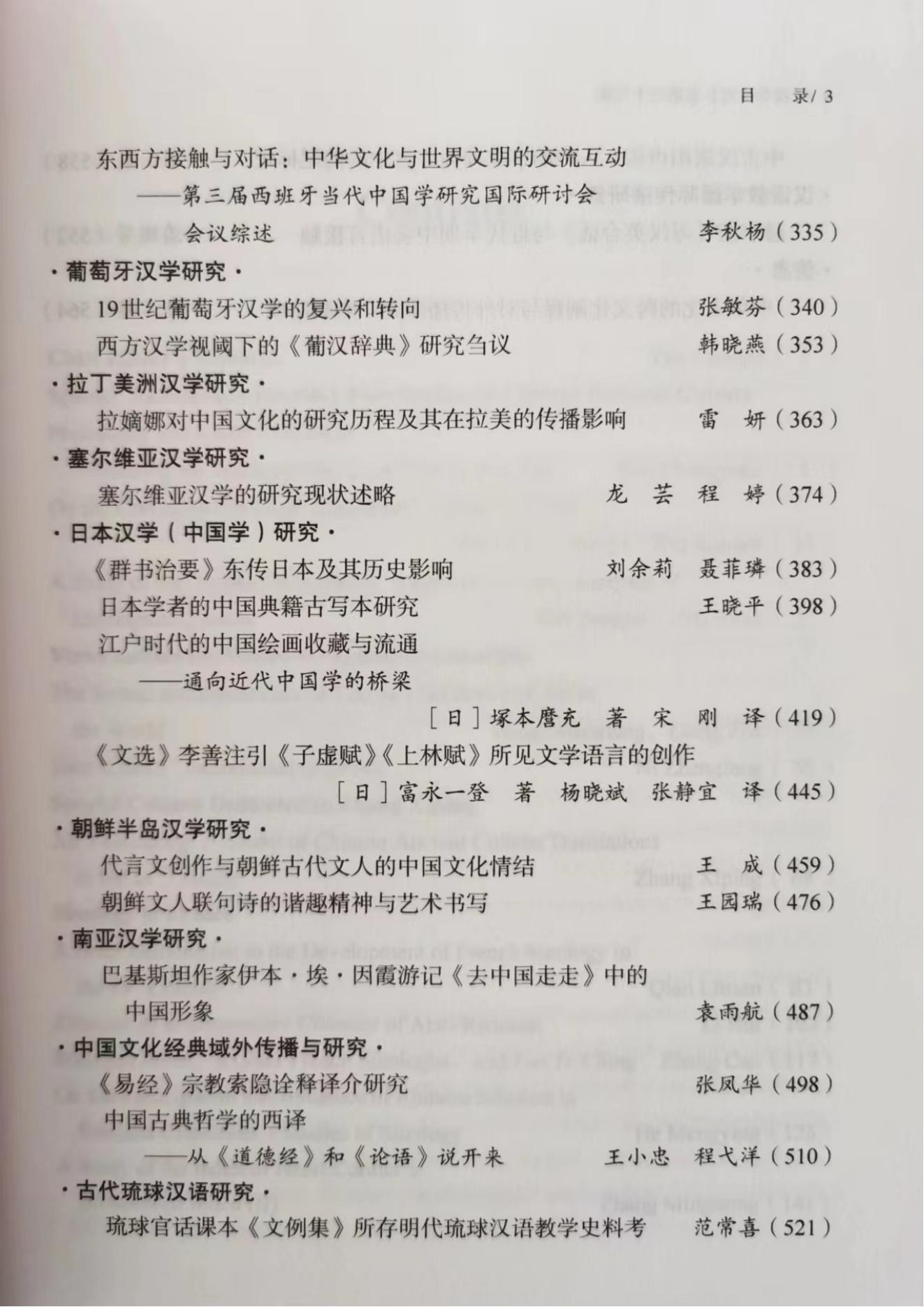
摘 要 :《群书治要》是一部汇集了六经至诸子中古圣先王治国理政智慧精华的匡政巨著,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唐玄宗天宝年间,日本遣唐使将其携回。由于《群书治要》重要的思想价值以及与盛世产生的内在联系,这部书被历代皇室、公卿所重视,并且经历了从皇室向民间逐渐普及的流传过程。从国家治理到思想传播,从汉籍出版到学术研究,《群书治要》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群书治要》东传日本的历史意义还体现在,它为中国保存下了这部珍贵却又亡佚的“帝王学”教科书,并几次将其传回中国,使这部治世宝典在当今时代继续发挥“古镜今鉴”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群书治要》 东传 日本 历史影响
2022年习近平主席致新年贺词时的右手边书架上,出现了一部极其珍贵却又鲜有人问津的经世之作——《群书治要》。其实早在2015年,这部书就已出现在习主席新年贺词的书架上了。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为求治国良策而令魏徵等社稷之臣,以“务乎政术”“本求治要”为宗旨,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从五帝至晋年之间经、史、子部典籍之中,撷取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而成的匡政巨著,成书于贞观五年(631)。唐太宗阅读手不释卷,感慨“览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并赐太子诸王作为从政龟鉴。《群书治要》不仅是魏徵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遗憾的是,《群书治要》传至南宋只余十卷残帙,《元史》已不见著录。这部书虽然在中土亡佚,但有幸在唐朝时被遣唐使携回日本保存并流传,成为日本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
1996年春,我国原驻日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影印天明版《群书治要》,由关学研究专家吕效祖等对其点校考译。《群书治要考译》的编纂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老先生的亲切关怀。2001年2月25日,习老先生亲笔为《考译》一书题词“古镜今鉴”,为继承和弘扬这部治世宝典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南,为其在当代的弘扬和传播揭开了新的篇章。据统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的用典来自《群书治要》的有82条之多。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和新理念也都可以从《群书治要》中找到其思想渊源。
《群书治要》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晶。梳理《群书治要》东传日本的来龙去脉,探究此书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课题,具有历史及现实意义。
一、《群书治要》东传日本
史料没有明确记载《群书治要》东传日本的时间及途径。尾崎康认为是奈良(710—784)至平安(794—1185)初期传入。金光一认为奈良时代天宝遣唐使(唐玄宗朝)和平安时代贞元遣唐使(唐德宗朝)携回此书的可能性较大。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深入史料进一步分析了两次东传的历史时机,认为天宝遣唐使一行最有可能将《群书治要》携回日本。
天宝遣唐使是日本第十一批遣唐使,由孝谦天皇于天平胜宝二年(750)任命,藤原清河任大使,大伴胡万和吉备真备任副使,天平胜宝四年(752,唐天宝十一年)闰三月出发,次年天宝十二年(753)三月藤原清河敬献方物,六月朝见唐玄宗。天平胜宝五年至六年(753—754)回到日本。金光一据《东大寺》所引《延历僧录》的记载分析,本次遣唐使受到了唐玄宗热情隆重的接待,特别是副使吉备真备拜秘书监,并由朝衡(阿倍仲麻吕)任使团参观向导,获赐进入宫廷秘府浏览群书的机会,因此有了发现《群书治要》的可能。《玉海》引《集贤注记》云:“天宝十三载(754)十月,(玄宗)敕院内别写《群书政要》,刊出所引《道德经》文。先是,院中进魏文正所撰《群书政要》,上览之称善,令写十数本分赐太子以下。”据此,天宝十三年之前,唐玄宗曾阅读《群书治要》并称赞有加,因此下令抄写并分赐太子以下。史料没有记载《群书治要》录副工作是否在遣唐使抵达之前完成,但此时朝衡已升任秘书监,又长期参与宫廷文献管理,理应悉知《群书治要》。又因朝衡与吉备真备同为第九批即开元五年(717)遣唐留学生,关系甚笃,很可能会向吉备真备推荐《群书治要》,而作为中国文献专家的吉备真备也很可能积极地将其携回。综上,金光一认为,“《群书治要》的东渡很有可能是由唐玄宗、吉备真备和朝衡的合作而成的,唐玄宗对这次使节的欢待,真备搜集和携回中国典籍的热情,以及朝衡对秘府藏书的知识,使得《群书治要》东传到日本。”笔者认为金光一的推断是合理的。
贞元遣唐使是日本第十七批遣唐使,由桓武天皇派遣,藤原葛野麻吕任大使,菅原清公任判官。贞元二十年(804)十二月藤原葛野麻吕抵达长安,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离开长安。《日本后纪》卷十二恒武天皇延历廿四年六月八日条详细叙述了此次使团行迹。金光一认为,虽然其中并无与《群书治要》相关的记载,但是不排除《群书治要》此时东渡日本之可能,并列出了三条依据:第一,作为纪传博士的菅原清公非常重视中国的帝王学,如果获知《群书治要》的存在,很可能积极地将其携回;第二,由《邺侯家传》所记唐德宗与李泌的对话知贞元遣唐使行时,唐秘府仍存藏《群书治要》,而且即使遭逢国丧,唐室对贞元遣唐使的款待不亚于天宝遣唐使;第三,日本皇室最早阅读《群书治要》是在承和五年(838),与贞元遣唐使时间相对接近。
金光一所列的三条依据,第一、二条可合并为对获得《群书治要》可能性的推测。笔者查阅史料后认为,虽然贞元遣唐使存在获得《群书治要》的可能,但实际上可能性很小。《日本后纪》卷十二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六月八日条记录:
廿四日,国信、别贡等物,附监使刘昴进于天子。刘昴归来,宣敕云:“卿等远慕朝贡,所奉进物,极是精好,朕殊喜欢。时寒,卿等好在。”
廿五日,于宣化殿礼见。天子不衙。同日,于麟德殿对见。所请并允。即于内里设宴,官赏有差。别有中使,于使院设宴,酣饮终日。中使不绝,频有优厚。
廿一年正月元日,于含元殿朝贺。
二日,天子不豫。
廿三日,天子雍王迨崩,春秋六十四。
廿八日,臣等于亟天门立仗,始着素衣冠。是日,太子即皇帝位。谅閻之中,不堪万机。皇太后王氏,临朝称制。臣等三日之内,于使院朝夕举哀。其诸蕃三日,自余廿七日而后就吉。
二月十日,监使高品宋惟澄,领答信物来,兼赐使人告身,宣敕云:“卿等衔本国王命,远来朝贡,遭国家丧事,须缓缓将息归乡。缘卿等频奏早归,因兹赐缠头物,兼设宴,宜知之。却回本乡,传此国丧,拟欲相见,缘此重丧,不得宜之,好去好去者。”事毕首途,敕令内使王国文监送,至明州发遣。
由上述记录知,贞元二十年(804年,延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使团朝见唐德宗,德宗对使团一行设宴、赏赐,“所请并允”。贞元二十一年(805)元旦,使团参加朝贺,再次见到德宗。正月二十三日,德宗病逝。国丧期间使团参与悼念。二月十日,唐皇室“赐缠头物,兼设宴”,随后使团离开。可见,使团在长安遭逢国丧,仅有短暂停留,未有较多活动,相比天宝遣唐使之行去之甚远。
笔者认为,使团两次朝见唐德宗,第二次朝见属于元旦朝贺,第一次是正式的使团朝见,因此更可能获得《群书治要》。获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使团向德宗提出请求,一种是德宗直接赏赐。第一种方式的前提是日本使节预知《群书治要》的存在,并且知道此书的价值,但目前尚未查得相关史料。第二种方式的前提是唐德宗对《群书治要》有所了解,且当时朝廷有副本存在。《玉海》引《邺侯家传》记载了李泌与唐德宗的对话:
上曰:“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广博,卒难寻究,读何书而可?”
对曰:“昔魏徵为太子略群书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谓之《群书理要》,今集贤合有本。又肃宗朝宰相裴遵庆撰自上古已来至贞观帝王成败之政,谓之《王政纪》,凡六十卷。比写本送臣,欲令进献于先朝,竟未果。其书见在,臣请进之,以广圣聪。”
上曰:“此尤善也,宜即进来。”于是表献。
由对话可知,当时集贤院尚存《群书治要》,但经过“安史之乱”,唐玄宗朝录副的《群书治要》劫后余存数量未知,难以判断是否尚存副本。而且德宗最终选择的是阅读《王政记》,因此可能并不了解《群书治要》,主动赏赐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总之,第一次朝见德宗时,虽有“所请并允”并设宴赏赐的记载,但是获得《群书治要》的可能性非常有限。
金光一的第三条依据是日本皇室最早阅读《群书治要》的时间在承和五年(838),与贞元遣唐使时间相对接近。笔者认为此说有待商榷。《日本の年号》“延曆”条云:
延曆の出典は不詳であるが、『群書治要』卷二六に「民詠德政、則延期歷」とある(その原拠は『三國志』魏書二五高堂隆伝。「歷」と「曆」とは通用。95永曆の項參照)。
据此,桓武天皇年号“延历”有可能出自《群书治要》,那么“延历”之前,《群书治要》就应该已传入日本。而贞元遣唐使之行在延历二十三至二十四年(804—805),就不可能是首次将《群书治要》携回了。此外,承和五年(838)是史料记载的天皇最早阅读此书的时间,但未必就是此书被阅读的最早时间。如果“延历”有可能出自《群书治要》,就可能存在天皇或臣子阅读此书而未记载的情况。天宝遣唐使于天平胜宝五年至六年(753—754)回到日本,此后不到30年即延历元年(782)。而贞元遣唐使回国的时间(805)与承和五年(838)相距却有33年。因此笔者认为,日本皇室最早阅读《群书治要》与贞元遣唐使回国的时间相对接近是值得商榷的。
结合《日本后纪》对贞元遣唐使之行的记载及日本学者对“延历”年号出处的推测,笔者认为,贞元遣唐使携回《群书治要》的可能性很小。天宝遣唐使之行,无论是当时唐皇室还是日本使团的情况,都有利于书籍传播,因此是最有可能将《群书治要》携回日本的,即《群书治要》于奈良时期天平胜宝五年至六年(753—754)传入日本。
二、《群书治要》在平安时期的流传及影响
《群书治要》传至日本后,日本天皇将其奉为圭臬,并确立了系统讲授此书的传统。史籍记载,平安时期有四位天皇阅读过此书。
仁明天皇是日本文献中首次记载阅读此书的天皇。《续日本后纪》第七卷记载,承和五年(838)六月壬子(廿六),“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正六位上直道宿祢广公读《群书治要》第一卷。有五经文故也。”仁明天皇热爱中国文化,“柱下漆园之说,《群书治要》之流,凡厥百家,莫不通览”。这一时期也成为日本皇室倾向中国文化的极盛时期。
清和天皇仰慕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意欲效仿,于是践祚翌年,天安三年(859)四月十五日庚子,改元“贞观”。《日本三代实录》后篇卷二十五记载,贞观十六年(874)闰四月二十八日丙戌,“顷年天皇读《群书治要》。是日御读竟焉。”贞观十七年(875)四月二十五日丁丑也有天皇阅读此书的详细记载。
尾张藩校督学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云:“谨考国史承和、贞观之际,经筵屡讲此书,距今殆千年。”朝散大夫国子祭酒林信敬《校正〈群书治要〉序》云:“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则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这充分说明《群书治要》在成就日本平安前期繁荣局面中所起的作用,也强调了大凡领导人民、事奉国君者是不可轻忽此书的。
宇多天皇阅读《群书治要》的记录见于现存最早的菅原道真传记《菅家传》:“(宽平)四年(892),……奉敕清凉殿侍读《群书治要》。”菅原道真道德文章皆为上乘,宇多天皇赞赏有加:“右大将菅原朝臣,是鸿儒也。又深知政事。朕选为博士,多受谏正”。宇多天皇重用原道真,整肃政纲,刷新政治,后世称为“宽平之治”。宽平九年(897)宇多天皇让位于醍醐天皇时,赠《宽平御遗诫》作为天皇之“金科玉条”。《遗诫》中有“天子……唯《群书治要》早可诵习”的劝勉之辞。
醍醐天皇谨遵父训。《日本纪略》第三(后编)记载:昌泰元年(898)二月二十八日戊辰,“式部大辅纪长谷雄朝臣侍清凉殿,以《群书治要》奉授天皇。大内记小野朝臣美材为尚复。公卿同预席”。醍醐天皇的臣籍皇子源高明私纂的仪式书《西宫记》将《群书治要》列为奉公之辈的设备之书。这不仅说明公卿大臣对《群书治要》的重视,也说明此时《群书治要》已不再囿于天皇及博士阅读。
从平安中期开始,日本天皇大权旁落,但也是在这一时期《群书治要》开始走出皇宫,进入京都贵族之家,这固然有治国理政的需要,阅读与传抄《群书治要》一时成为京都贵族的时尚。现存最早的《群书治要》文本,便是由京都贵族“五摄家”之一的九条家代代保管的平安本《群书治要》(又称九条家本)。
平安本于“二战”后被发现于九条公爵府邸的一间仓库,余13卷残帙,抄写于10或11世纪,是当前《群书治要》最古老的写本,文献价值极高。其所用纸张属于高贵的御用材料,书写风格优雅端正,这种风格多见于平安时代抄写的和歌典籍,汉籍则少见,因此推测平安本《群书治要》是在特殊情况下制作。也正是由于高贵的用纸及精美的笔迹,九条家经常将卷子切割后作为珍贵的礼物献给天皇、贵族或赠与友人,成为“古笔切”藏品,这导致平安本《群书治要》多有散佚,但也说明了其珍贵的文物价值。根据平安本《群书治要》残简的散佚及残卷奥书的记载,《群书治要》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有着广泛的阅读和传抄,可见,《群书治要》中有关治国理政的思想在日本古代获得了广泛认可。1952年,平安本《群书治要》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三、《群书治要》在幕府时期的流传及影响
镰仓幕府(1192—1333)至江户幕府(1603—1867)这段时期,天皇权力被架空,政治实权在幕府手中。直至明治维新,与《群书治要》相关的记载多集中在幕府。
(一)镰仓幕府时期
幕府非常重视学问,据佐川保子,平安末期至镰仓幕府时期,教授天皇的汉籍有《古文尚书》《古文孝经》《后汉书》《贞观政要》《帝范》《臣规》《白氏文集》等,教授“公卿、将军等特定贵人”的书籍除上述外,还有《春秋经传集解》《论语》《群书治要》。
镰仓幕府的文化遗产中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由北条实时创建的金泽文库。金泽文库是日本中世纪武家文化之代表文库,收有日、汉典籍两万卷以上,素有“和汉文物之渊薮”之称。从北条实时到其孙北条贞显时期的写本,是金泽文库中最为古老的组成部分,金泽本《群书治要》亦是此时产生的珍贵典籍。
建长五年(1253),北条实时委托后藤基政抄写了《群书治要》全帙,又命三善康有抄写副本。文永七年(1270)十二月,原本史部多卷被焚毁,随后根据副本进行了补抄。14世纪初,北条贞显发现仍有一些卷子不存,便利用自己在京都任职的机会,借出藤原光经和藤原经雄(藤原俊国之子)的藏本补抄。
北条实时还委托清原氏家族和藤原氏家族的学者为金泽本《群书治要》添加了训点。清原教隆为经部诸卷添加了训点,并多次传授北条实时。金泽本卷一奥书云:“建长七年(1255)八月十四日,蒙洒扫少尹尊教命,加愚点了。……同年九月三日即奉授洒扫少尹尊阁了。”说明八月十四日清原教隆加点完毕后,九月三日即开始向北条实时教授此卷。据小林芳规,传授并不仅限于九月三日这一次,各卷末类似备忘录风格的横线(“读符”)表示传授或解读的次数。由此可知经部各卷中,卷一传授六次,卷三五次,卷五、六各四次,卷七、九、十各两次。
史部训点者是藤原氏南家的藤原茂范,以及藤原氏北家系统内麿流日野家的藤原俊国。由于史部多卷属于补抄,因此无法知晓北条实时是否学习过。但从移录底本奥书的内容可知对底本《群书治要》(非金泽本,而是《群书治要》其他藏本)的阅读与传授情况,如卷廿九奥书记载文永八年(1271)藤原经雄阅读了此卷,卷三十奥书记载藤原经雄传授了此卷。这说明当时对《群书治要》的学习是比较普遍的。
子部的训点是清原教隆根据莲华王院宝藏御本移写的,而御本的训点除卷册六由清原赖叶(教隆的祖父)添加外,其他诸卷是由藤原氏式家宇合流的敦周、敦经和敦纲添加的。根据“读符”,清源教隆将卷卅六、册一至册三、册五至册六、册八至五十各以一次传授给北条实时。
从金泽本奥书可知,12世纪末至14世纪初,日本皇室、京都贵族以及幕府有众多《群书治要》藏本,而且从天皇、博士家,到幕府将军、御家人,都对学习《群书治要》有着浓厚的兴趣,不断进行抄写、点校、阅读。
1333年,镰仓幕府灭亡。此后日本经历了室町幕府及战国时代,时局变乱,众多《群书治要》抄本纷纷失散,至江户幕府德川家康时,金泽本《群书治要》成为了海内孤本(卷四、十三及二十已亡佚),这也使金泽本成为了此后诸《群书治要》版本的母本。
金泽本《群书治要》是日传汉籍中的瑰宝。如果同时考虑年代和保存情况,金泽本《群书治要》目前是“最古的全本”,其在文献学、文字学和中国古代治道思想方面,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二)江户幕府时期
德川幕府的将军、幕僚等皆注重文治,尤其注重《群书治要》的阅读和刻印,出现了庆长、元和、天明、宽政、弘化等众多《群书治要》版本。
1.庆长一元和年间
《群书治要》能够在江户时期重振光辉,与德川家康的积极推动密不可分。德川家康虽出身武家,但喜文翰,确立了“文治武功”的基本治国策略。特别是认识到印书在文治中的积极作用,退居骏府后,便倾力于铜活字印刷。其实早在庆长年间,德川家康就已经开始重视《群书治要》。庆长十五年(1610)九月,德川家康下令将金泽本《群书治要》抄写两份,作为制定公家、武家法度的参考,并按照唐太宗编纂此书的目的加以利用。这便是庆长本《群书治要》,此本后来成为元和本《群书治要》的底本。
元和本《群书治要》是德川家康于元和二年(1616)正月十九日下令印刷的,也是家康下令印刷的最后一部汉籍。金光一据《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认为,元和本《群书治要》的印刷政治色彩浓厚。《法度》是关于江户幕府与天皇及公家之间关系的法律,第一条“天皇の主务”规定天皇在各种技艺能力之中应当以研习学问为先,并援引《宽平御遗诫》云,天子虽不穷经史,但可诵习《群书治要》。然而《群书治要》此时只有金泽本这一孤本了,因此江户幕府要流布《群书治要》,首先需要印书,这便有了元和本的刊印。
德川家康不仅下令刊印《群书治要》,还命林罗山补足《群书治要》所缺之卷。“元和元年(乙卯),先生(林罗山)赴骏府奉命监《群书治要》等刊版之事,且补足治要阙失之数卷。”或许是元和本刊印之时,林罗山补缺工作尚未完成,因此元和本《群书治要》仍为47卷。
元和本《群书治要》于元和二年(1616)五月底成书,用时四个多月,可谓非常迅速。然而在此之前的四月十七日,德川家康在骏府城猝然逝世,生前仅见部分刊印成果,遗憾未见书成。元和本也未得奉命流布于世,而是随其他藏书一起,被分赠给家康的儿子。其中铜活字传纪伊家,印本传尾张、纪伊两家。
元和本《群书治要》不仅是日本首次大规模印刷《群书治要》,而且在日本印刷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元和本《群书治要》47卷及《大藏一览》10卷又称为骏河版,骏河版是日本近世三大官版之一,官版的兴起是日本于数百年动乱之后振兴文教的标志之一。骏河版还是首次用日本铸造的铜活字印制的典籍,中国人林五官担任技术指导。
2.天明一宽政年间
在尾张藩藩主、幕僚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群书治要》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大量刊刻和广泛传播。天明本《群书治要》是在尾张藩第九任藩主德川宗睦的主张下,由其世子、幕僚通力合作完成的。宗睦深知《群书治要》对日本平安时代繁荣做出的贡献,然而元和本未得广布,且由于排印仓促,讹谬多有,因此命二世子治休、治兴与臣僚等校正刊印此书。
工作于安永年间开始,然而二世子先后于1773、1776年去世。安永六年(1777),高须藩的德川治行过继成为尾张藩世子,继承前二世子遗志,继续刊行。参与刊印的人员有人见桼、深田正纯、细井德民、冈田挺之、关嘉、南宫龄等,皆为尾张藩重臣、藩主侍读、藩校明伦堂督学或教授。可见,尾张藩为保证校勘质量,集中了整个藩国最有学问的学者参与。
校勘时,“博募异本于四方”,“上自内库之藏,旁至公卿大夫之家,请以比之,借以对之。”“内库之藏”“公卿大夫之家”当指枫山文库所藏的金泽本及九条家所藏的平安写卷,四方异本指魏徵所引原典的传世本。故校勘是以元和本为底本,与金泽本、九条家本进行校合,再与传世原典相互对照。天明六年(1786)十月完成校勘,历时约10年。
天明七年(1787)九月中旬印刷完成。据尾崎康,初印数量有五六十部(据《细井平洲书简》)和三百部(据《名古屋市史》)两种说法。刊印完成后,藩国重臣、校勘者、有关人员各赐一部。第二年,又有七十多位藩臣申请获得此书。随后多次补印。宽政三年(1791),尾张藩再次组织学者对原文进行了校勘,此次补印数量较大,此即宽政本《群书治要》。后享和、文化、文政年间,尾张藩又多次补印。在《群书治要》诸版本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天明本和宽政本。
《群书治要》在日本大量印刷后,日本学界注意到此书在中国已失传,便积极将其传回中国。首次回传是在嘉庆元年(宽政八年,1796),据近藤守重记载,德川宗睦幕臣人见桼将五部《群书治要》委托其送予中国。守重与当时长崎地区行政长官中川忠英商议后,将五部中的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存诹访神社,三部委托唐商馆转交中国。此次回传的是宽政本。此本或其再刊本被阮元巡抚浙江时访得,收入《四库未收书》,上呈嘉庆皇帝。至此,在中国散佚失传了近千年的《群书治要》重回故土。《群书治要》不仅再次传入皇室,而且作为一部“佚存书”,在清末学术界,特别是在辑佚和校勘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3.弘化年间及近现代
纪伊藩也积极推动《群书治要》的弘传。德川家康注重文治,尤其重视《贞观政要》及《群书治要》,纪伊德川家欲继承德川家康祖训,使国老、诸司知书中大意,以有裨益于政治,于是刊印二书。在骏河版《群书治要》刊印230年后,纪伊藩用元和二年的铜活字再次刊印《群书治要》,弘化三年(1846)仲春竣工。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现代化的开端。明治二十四年(1891)三月三十日,金泽本《群书治要》入藏宫内省图书寮(即宫内厅书陵部),由皇室永世保存。昭和十六年(1941),宫内省图书寮以金泽本为底本,精细校勘,铅字排印了昭和本《群书治要》。根据《群书治要解说》可知其刊行目的:《群书治要》作为治世宝典,对成就盛世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李唐之治有赖此书,日本历代皇室及公卿都极为重视。然而金泽本孤本流传,且有大量异俗体字;而其他版本又多有讹误,因此以金泽本为底本,将《群书治要》再次校勘出版。同年(1941),宫内省图书寮还运用珂罗版技术复制了金泽本,复制本被分赠给日本各地图书馆及研究机构收藏,金泽本《群书治要》全面公开。
随着日本政府建立公共图书馆,统一管理原官家及众多私家藏书,藏于不同文库的各种版本的《群书治要》也随文库的开放进入公众视线,广大学者得以近距离阅读此书。此后,《群书治要》不仅在日本学界,也在中国学界收到了广泛关注,书志学、出版学、校勘学、文献学、版本学、语言学、历史学及思想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大量涌现。
结 语
《群书治要》在唐玄宗时期传到日本后,不仅成为日本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还在此后的日本历史中,从国家治理到思想传播,从汉籍出版到学术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保存下了这部珍贵却又亡佚的“帝王学”教科书。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无偿捐赠了36部4175册汉籍,《群书治要》赫然在列。细川先生墨书题写“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宣明了文化典籍的重要功用。
《群书治要》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独特创造、价值理念等,简要翔实地表达了出来,是一部汇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次经之书”。书中所蕴藏的治国理政思想,特别是关于国家盛衰的经验和规律,是历经数千年考验所累积的结晶,历久弥新。正如魏徵所赞叹的,此书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群书治要》中的德福观研究”的成果,批准号(19BZX123 )。为方便阅读,本文略去引注】